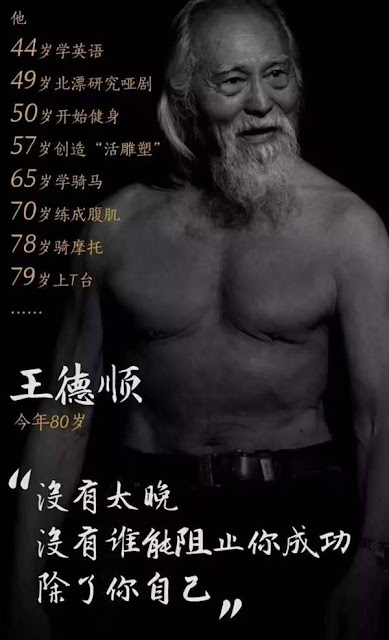我深信一般人其實或多或少有些精神病,只是我們患病的程度不致影響他人,因此可以輕易隱藏起來,無須去跟進,不過身邊人的生活飽受精神病而受到影響,每個活著的都曾經有自己的經歷,抑鬱症是常見得到,曾經悲傷過,焦慮過,或者因為悲傷太過沉重,甚至曾暗暗動過想要結束生命的念頭,懷疑過自己是否得了抑鬱症

談到抑鬱症,自從成年之後,越來越喜歡閱讀題材講悲傷的作品,原因不是長大了人就變的更悲傷了,而是因為長大了之後,人就越來越不懂得,也越來越不敢表達自己的悲傷了。
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不允許人隨便悲傷的,悲傷會被人打上了羞恥的烙印。
如果一個人已經長大了,情緒模式似個孩子一樣,一不高興就發脾氣,大吵大鬧,就會被人說是中二,矯情,不成熟,不獨立,不懂控制情緒,又或是太作,太弱,太玻璃心。
巨大的社會之中,工作環境怕人散佈負能量,一旦知道你有精神病,那怕是抑鬱,於是,人們就會像躲避瘟疫那樣的紛紛離你而去。即便是曾說過愛你,會陪著你,會懂你的人,也未必能忍受你傾訴悲傷,展露殘缺。他們欣賞的,是那個自信的你,聰明的你,堅強的你,美麗的你,幽默的你,大氣的你,唯獨不是那個真正的你。
就像聊齋裡的主角,愛的只是美人一張皮,當他看到畫皮下的鬼魅真相時,都只會嚇的驚慌失措,落荒而逃。

我懷疑有些人不是沒有悲傷而是他們個人意志強大到一個點,強迫自己克服了負能量,但不是所有魚都活在同一片海的。
嗯,我說的負能量,似乎就是那樣鬼魅的存在。
原本看似開明的社會裡,鼓吹包容一切價值觀的現代社會裡,唯一不能被包容的就是負能量,它成為一種絕對的不正確,不道德,不光榮。
「你唔好唔開心」「往前看」「同你去咩咩咩(一些好玩的活動),會開心返」這些話對一個有抑鬱的人來說,其實無補於事,他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治療安寧。

抑鬱彷是一道隱秘處的傷口,哪怕再痛也得咬牙忍住,不可輕易露出痕跡,等到夜晚無人處,再輕輕撕開被血滲透的內衣,咬牙給傷口消毒換藥,靜靜在心裡對它說,好起來吧。
古今中外,悲傷的詩句千古流傳,可你環顧身邊,卻找不到一個悲傷的人,大家都在忙著表達我過得很好,我生活多美好。那麼,流行歌曲中的悲傷到底是誰在偷偷的聽呢?
這倒是現代社會的咄咄怪事。悲傷成為了所有人公開的秘密,卻又是每個人緘口不提的心事,明明悲傷的情歌鋪天蓋地,
不如意事常八九,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難過悲傷真有如此不體面嗎?現代人就連SM都已經不再被視為羞恥,反面當成正當的性欲望,但什麼時候,悲傷才能不再被視為羞恥呢?
林夕很多歌都是寫一個人的悲哀愁緒,我們在K房都會唱,可是我們不會公開說,文學歌曲凡是涉及悲傷的作品,總是令我看得覺得格外貼心,在世界上找一個能夠傾心相待的朋友不易,唯有在文字的媒介中,永遠保持著一個安全的距離,人們才能彼此親近。

無論是悲傷的小說,還是電影,或者音樂,總之那是一種普遍性的悲傷,不涉及任何個人的具體的細節,因此也就不存在恥辱和批判。人們就可以在這種普遍的悲傷中尋求一些短暫的共鳴,但真正的悲傷卻永遠秘而不宣。
現代社會是一個瘋狂的社會,是一個把成功與美德捆綁在一起的社會,一切都在頌揚“更高更好更強”,人們都簇擁在成功者的身邊,沒有人會去領會那些被時代拋在身後的人。貧窮和失敗,曾經可以歸咎於命運,如今卻只能責怪自己的無能。因此,這個時代的人,也更容易感受到存在的焦慮,以及永遠不敢停止的前進的壓力,我們前所未有的渴望著他人的尊重,而悲傷的情緒卻與這一切背道而馳。
現代社會是一個瘋狂的社會,是一個把成功與美德捆綁在一起的社會,一切都在頌揚“更高更好更強”,人們都簇擁在成功者的身邊,沒有人會去領會那些被時代拋在身後的人。貧窮和失敗,曾經可以歸咎於命運,如今卻只能責怪自己的無能。因此,這個時代的人,也更容易感受到存在的焦慮,以及永遠不敢停止的前進的壓力,我們前所未有的渴望著他人的尊重,而悲傷的情緒卻與這一切背道而馳。
阿蘭‧德波頓在《身份的焦慮》中,曾寫到:
“在古典社會裡,底層的僕人能泰然地接受他們的命運,愉快地生活,並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,同時也不失自尊。然而,在一個民主社會裡,有的只是報刊和社會輿論沒完沒了的鼓噪,讓每個生活在底層的人都相信他們總有機會攀上社會金字塔的塔尖,有機會成為實業家、大法官、科學家,甚至總統。這種無限機遇的論調在一開始也許能給人一種盲目的樂觀,對那些底層的年輕人尤甚。但在他們之中,只有極少數最優秀的幸運兒才有機會脫穎而出,實現他們的夢想;而多數的人,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,他們並不能改變自己的身份,他們會轉而變得意志消沉,內心極度痛楚,並輕賤自己,一旦他人停止對他們表示尊重,他們就很難對自己繼續懷有信心。”
所以,比起對他人悲傷的不寬容,我們更多的是對自己悲傷的不寬容。
也許偶爾,也曾要和誰談談心裡話,傾訴所承受的壓力。但心裡會突然有個微小的聲音提醒自己:別人真的會在乎嗎?

也許會表現出同情的樣子,但又有多少人能真的感同身受呢?即使感同身受,又能為你改變現狀做些什麼呢?大多數人無非收穫一些同情的眼神,拋下幾句根本落不到實處的安慰。
但更多的也許只是暗暗的鄙視,更有一些看熱鬧的路人,會在心裡,或背地裡去這樣討論:
「你看,她又在作了,我看她難過都是咎有自取啊。,」
「還以為他生活過得多好,原來都還不如我一半,放心了。」
最後,自己的遭遇還是要自己承受,自己的無奈也只能自己消化。既然如此,還不如一開始就選擇沉默好了。所以,抑鬱就這樣開始成為一種不動聲色蔓延的疾病,抑鬱,不是悲傷的氾濫,而是對悲傷的拒絕。

當很多明星因為抑鬱症自殺之後,很多人提起對他們的印象,通常都是吃驚的。事前根本看不出來啊?平時性格很好啊,非常有教養,會照顧他人,溫柔有禮貌,甚至非常逗比。卻不知正是這樣的人,才最容易抑鬱,因為越是對自己要求高,要求完美的人,對於悲傷和軟弱,就更是懷有深重的歧視。普通人能在一定程度忍受自己的不完美,包容自己的軟弱和殘缺,接受生活的平庸與粗俗,他們卻不能。

他們對自己要求太嚴格,甚至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潔癖,不會允許悲傷這種“不良情緒”存在太久,而是會想盡辦法去壓抑它,驅趕它,否認它。他們比起普通人,更善於把悲傷藏的密不透風,面對世界只露出燦爛的笑臉。
所以,面對悲傷,不要再告訴自己,我要堅強,我要爭氣,不是的。而是要允許自己悲傷,認真的與悲傷進行一場面對面的談話。
對我來說,情緒是要去抒發,我去寫作,去做運動,去學自己感到有趣卻有點難度的事,當然都可以找人傾訴,或者僅僅是痛快的哭一場,好好的睡一覺,讓自己看到,到底是什麼令你如此悲傷?

你能夠解決它嗎?如果不能解決,能夠理解嗎?如果複雜到連理解也不能,那麼就允許它暫時的存在,不時的回來和它再次對話,就像腫瘤,它是可以切除的,可以化療的。最終它就會在你的直面中漸漸縮小,遠去,也許永遠不會徹底消失,但終會縮小到不再影響你生活的程度。
內心的自尊、浮世的名利,都讓人不快樂不安息地爭競無休無止,但人生短短的幾十年,贏的到底能贏到多高?人為什麼要如此你死我活,踩低拜高,幸災樂禍,而不是在別人悲傷的時候,多給予一點溫柔的傾聽、接納和包容呢?
我天性不是溫柔隨和的人,但依然希望認識更多負能量及抑鬱的人,把自己殘餘的耐性捐出來,將來若還有人記起我,也會說一句,啊,他曾經傾聽過我的悲傷,他是個溫柔的人。
接著,我會跟自己所參與開的義工團Rotaract Club of City Northwest Hong Kong 港城西北扶輪青年服務團,會在2016年10月8日(星期六)舉辦一個「真人圖書」活動,親身與精神病康復者互動,一個深度對話,從而真正達到傾聽別人。

“在古典社會裡,底層的僕人能泰然地接受他們的命運,愉快地生活,並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,同時也不失自尊。然而,在一個民主社會裡,有的只是報刊和社會輿論沒完沒了的鼓噪,讓每個生活在底層的人都相信他們總有機會攀上社會金字塔的塔尖,有機會成為實業家、大法官、科學家,甚至總統。這種無限機遇的論調在一開始也許能給人一種盲目的樂觀,對那些底層的年輕人尤甚。但在他們之中,只有極少數最優秀的幸運兒才有機會脫穎而出,實現他們的夢想;而多數的人,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,他們並不能改變自己的身份,他們會轉而變得意志消沉,內心極度痛楚,並輕賤自己,一旦他人停止對他們表示尊重,他們就很難對自己繼續懷有信心。”
所以,比起對他人悲傷的不寬容,我們更多的是對自己悲傷的不寬容。
也許偶爾,也曾要和誰談談心裡話,傾訴所承受的壓力。但心裡會突然有個微小的聲音提醒自己:別人真的會在乎嗎?

也許會表現出同情的樣子,但又有多少人能真的感同身受呢?即使感同身受,又能為你改變現狀做些什麼呢?大多數人無非收穫一些同情的眼神,拋下幾句根本落不到實處的安慰。
但更多的也許只是暗暗的鄙視,更有一些看熱鬧的路人,會在心裡,或背地裡去這樣討論:
「你看,她又在作了,我看她難過都是咎有自取啊。,」
「還以為他生活過得多好,原來都還不如我一半,放心了。」
最後,自己的遭遇還是要自己承受,自己的無奈也只能自己消化。既然如此,還不如一開始就選擇沉默好了。所以,抑鬱就這樣開始成為一種不動聲色蔓延的疾病,抑鬱,不是悲傷的氾濫,而是對悲傷的拒絕。

當很多明星因為抑鬱症自殺之後,很多人提起對他們的印象,通常都是吃驚的。事前根本看不出來啊?平時性格很好啊,非常有教養,會照顧他人,溫柔有禮貌,甚至非常逗比。卻不知正是這樣的人,才最容易抑鬱,因為越是對自己要求高,要求完美的人,對於悲傷和軟弱,就更是懷有深重的歧視。普通人能在一定程度忍受自己的不完美,包容自己的軟弱和殘缺,接受生活的平庸與粗俗,他們卻不能。

他們對自己要求太嚴格,甚至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潔癖,不會允許悲傷這種“不良情緒”存在太久,而是會想盡辦法去壓抑它,驅趕它,否認它。他們比起普通人,更善於把悲傷藏的密不透風,面對世界只露出燦爛的笑臉。
所以,面對悲傷,不要再告訴自己,我要堅強,我要爭氣,不是的。而是要允許自己悲傷,認真的與悲傷進行一場面對面的談話。
對我來說,情緒是要去抒發,我去寫作,去做運動,去學自己感到有趣卻有點難度的事,當然都可以找人傾訴,或者僅僅是痛快的哭一場,好好的睡一覺,讓自己看到,到底是什麼令你如此悲傷?

你能夠解決它嗎?如果不能解決,能夠理解嗎?如果複雜到連理解也不能,那麼就允許它暫時的存在,不時的回來和它再次對話,就像腫瘤,它是可以切除的,可以化療的。最終它就會在你的直面中漸漸縮小,遠去,也許永遠不會徹底消失,但終會縮小到不再影響你生活的程度。
內心的自尊、浮世的名利,都讓人不快樂不安息地爭競無休無止,但人生短短的幾十年,贏的到底能贏到多高?人為什麼要如此你死我活,踩低拜高,幸災樂禍,而不是在別人悲傷的時候,多給予一點溫柔的傾聽、接納和包容呢?
我天性不是溫柔隨和的人,但依然希望認識更多負能量及抑鬱的人,把自己殘餘的耐性捐出來,將來若還有人記起我,也會說一句,啊,他曾經傾聽過我的悲傷,他是個溫柔的人。
接著,我會跟自己所參與開的義工團Rotaract Club of City Northwest Hong Kong 港城西北扶輪青年服務團,會在2016年10月8日(星期六)舉辦一個「真人圖書」活動,親身與精神病康復者互動,一個深度對話,從而真正達到傾聽別人。